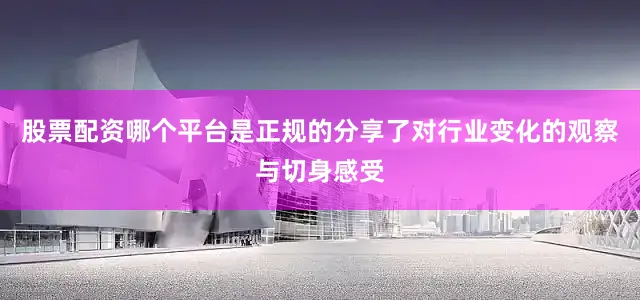江青大声说:“我瞧不起你!”
我也看不起你!
当那段“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拉开序幕之际,我曾有幸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任职数月。
随着该小组的崛起与持续扩张,其口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仅与广大民众为敌,其内部关系亦充斥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斗争。作为共产党的一员,这恐怕是我所见过的最为无政府、最为混乱的组织。
笔者作为历史当事人,从陈伯达和江青的明争暗斗这个角度,披露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内幕。

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组的四位杰出成员,从左至右依次为戚本禹、王力、关锋与穆欣。
01 伙同江青在“中央文革”排除异己
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如坚持党的领导还是取消党的领导(“踢开党委闹革命”)、稳定军队还是搞乱军队、对干部“打倒一切”还是区别对待,以及在工作组存废、炮轰刘邓或是保刘邓等等问题上,都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和斗争。
总的来说,这场争论的核心在于“求乱”与“惧乱”两种观点的交锋。在此过程中,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等人屡次与江青发生争执。
1966年11月29日,江青突然召集科委系统举行了一场万人大会,却未事先告知负责科委事务的聂荣臻和陶铸。陶铸得知消息后,匆匆赶至会场,质问江青:“为何事先不通知一声?”
江青面色骤变,怒气冲冲地破口大骂:“你敢怒,便是要造你的反,意图将你推翻!”
陶铸持续抵制江青错误言行。
江青凭借其权势,独断专行,强令周围之人唯命是从,不容许任何异议的存在。对于她不喜、疑虑或视作不顺从之辈,她一律予以排挤和迫害。
1967年年初,江青伙同林彪刮起“一月夺权”风暴之前,接连把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打倒”,赶出中央文革小组,唆使造反派对他们揪斗,进行残酷迫害。小组成员尹达、谢镗忠也都受到江青的打击迫害离开这个小组。

陶铸、江青、曾志、毛泽东
江青扬言:
“无论何人,一旦触犯了我的信任,便无法再维系这份关系。”
她将小组办事处的七位历任组长中的六位送入了牢狱,仅剩最后一位,即她的女儿李讷,得以幸免于难。
更有十四名员工被投入了牢狱,其中不乏江青的警卫员孙立志,他因被诬陷“窃取”了江青的钥匙而蒙冤,在经历了七八年的牢狱之灾后,最终被送往劳改场所继续服刑。
中央文革小组这种混乱状态,不但引起小组成员的不满,也受到毛泽东多次批评,他批评这个小组没有建立制度,没有民主集中制,小组没有作过正式决定,不但内部没有民主集中制,对上也没有报告。
毛特别是对江青、陈伯达擅自打倒陶铸一事非常生气。他说:
陶铸确实犯了错,然而却未先行与我沟通,便突然对外揭露。既未向上级汇报,亦未与干部群众进行充分商议。
毛在2月6日会上严批。
你们的文化革命小组缺乏政治和军事经验。在老干部普遍被打倒的情况下,你们真的能胜任掌权吗?
江青仰望苍穹,世间能入她眼者寥寥无几。陈伯达与江青对我从未有过劝诫,一个主张适度收敛,另一个对干部持宽容态度。一旦出错便予以罢黜,甚至自责至极。难道你们就从未犯过错吗?
毛泽东又在10日的会议上,当面严厉批评陈伯达和江青,火气更大。他气愤地说:
你这陈伯达,竟敢一举将一位常委扳倒,接着又要对付另一位!
你这江青,好高骛远,眼高手低,胸怀大志却才疏学浅,你似乎只关注着那唯一一人!
陶铸被打倒,其余人皆安然无恙,唯独你们二人之事引人注目。
查阅了相关记录,发现多数人要么缺席,要么缄口不言。唯有陈伯达发表了言论,江青则不时插话其间。
毛泽东决定立即把张春桥、姚文元从上海召回北京,由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和江青。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使中央文革小组乱了阵脚,慌作一团。
陈伯达显得异常焦虑,他曾坦言自己几欲轻生,抱怨道:“江青逼迫得我难以继续生存。”此外,他还向人透露,经过查阅资料,他发现马克思的女婿,法国的拉法格,亦因自杀而离世,而列宁还曾对他表示纪念,这无疑证明了共产主义者亦有权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至于在打倒陶铸的会议上发言一事,他声称自己事先毫不知情(实际上确实如此,这是江青一手策划的)。他在服用安眠药后未能醒来,以至于在昏迷中胡言乱语。

陈伯达和江青
2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了会,江青躲起来,装病不参加,会上只批评了陈伯达,根本没有批评江青。大家知道陈伯达想要自杀,会开得马马虎虎,不再批评他。
会议结束后,江青听闻陈伯达意图自尽,便如同狂怒的疯子,指着陈伯达的鼻尖,怒斥不止。
“你选择结束生命,这将导致你的党籍被剥夺,成为背叛者。你真的敢这样做吗?”
(在未来的某次人大会堂东大厅的会议上,江青公然宣称,她要强行取下陈伯达将军制服上的帽徽和领章。)
江青对毛泽东的批评只当耳边风,事后仍然我行我素,为所欲为。中央文革小组继续坚持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到处煽风点火,搞乱全国,终于造成全国混乱的局面,无政府主义发展到无法收拾的程度。
02“文革小组分裂正式公布”
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位均出身于《红旗》杂志社,系陈伯达亲自甄选加盟的骨干成员。王力曾任该社副总编辑,关锋为其得力助手,戚本禹亦为杂志社的佼佼者。然而,抵达此处后,他们却纷纷向江青靠拢,对她言听计从,成为她身边得力的助手,与陈伯达的关系日渐疏远,对立之势渐显。
陈伯达说:
有一次“《红旗》杂志接到北大校文革勒令公布发表《黑修养》的经过。在这文件上签署同意的,有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送到我这里,我特别写了三个大字:‘不同意’。
王力、关锋、戚本禹鼓动江青向我提出询问,我回应道,若一家党刊屈服于某个学校团体的“强制命令”,难道不感到有失尊严吗?
江青理亏词穷,无法辩驳。然而翌日,她却再次送来关锋整理的一些所谓材料。
所谓北大勒令事件,终于揭开文革小组分裂的序幕,宣告他们再也无法虚伪地共处一室。
所谓的“王关戚”案件便是这样逐步浮出水面,这一过程至少标志着文革小组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那些伪装的面具终于被揭开。

江青、康生、陈伯达
此事给陈伯达留下了深刻的痛楚印象,即便时过境迁,在其撰写的《“文革”中若干重要事情》一书中,仍不时提及,感慨良多。
“以一例而言,或许能勾勒出‘文革小组’的日常情景:北大‘校文革’向《红旗》杂志发出‘勒令’之际,江、关、戚三人未曾召集会议商议,便毫不犹豫地签署了接受‘勒令’的文件,随后再将之交至我手。显而易见,他们自认占据多数,因此一切决策均应顺从他们的意愿。”
周恩来每当参加规模较大的群众集会,总会提前告知中央文革小组,请求指派专人陪同。多数情况下,他会亲自拨打电话进行安排,只有在极其繁忙的时刻,才会委托秘书代为处理。他总是按时到达会场,即便中央文革小组指派的陪同人员未能按时抵达,他也会在休息室内耐心等候。这种细致入微的态度,不仅体现了他一贯的严谨作风,亦是为了避免江青等人找到任何挑刺的借口。

有一次中央文革小组开会,谈到派人陪同总理活动的事,江青指着戚本禹和姚文元说:“总理常要小组派人去陪,你们年轻,不要去,可以由春桥、关锋、穆欣他们去。”实际上,张春桥和关锋从来不去,十有八九都是由我去陪。
1966年9月21日,我国总理于中南海亲切会见了来自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群众组织代表。关锋同志彼时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总理特地拨通了电话,邀请他一同出席。然而,关锋同志当时正闲暇之余,却毅然决然地拒绝了总理的邀请,坚持不前往。
总理在那边耐心等待,电话催促已达三次以上。当时我身兼办公室职务,遂不得不前去催促。
“总理久等不妥。”
关锋瞪眼板脸回应:
“我就是不去陪他!”
此外,恰逢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之际,会议地点设于人民大会堂,特邀请总理莅临。总理事前亲自致电陈伯达(同时兼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敦促其与会。会议时间定于当日下午三时。陈伯达起初要求戚本禹陪同出席,但戚本禹婉拒。随后,他将陪同人选更改为关锋,关锋亦表示不便前往。
陈伯达与关锋同居于15楼,秘书王保春随他从二楼步下,便派办公室的瞿怀明前去唤关锋。然而,关锋却坚持卧床不起,屡次催促之下,他依旧拒绝起身。陈伯达感到无奈,遂乘车前往16楼,于办公室静候,命王保春上楼去唤戚本禹。戚本禹亦在床上假寐,经秘书唤醒后,亦坚称不去。
王保春屡次劝慰,戚氏方才缓缓下楼,他转而对陈伯达言道:“我断然不去,去了便是等同于认可(科学院革委会)的举动!”

陈伯达热切地邀他同行,但戚竟坚决地予以回绝,并当众对那位“组长”进行了一番严肃的训诫:“若是你想去,那就由你去吧,你身为科学院副院长,自当出席!”言外之意,无需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身份出席。他狂傲的姿态,显露无遗。
陈伯达步入人民大会堂118室,向总理表达了他的担忧:“他们均未到来,我亦不便与众人会面。”总理见到他这般踌躇,便不忍苛责,回应道:“你只需与主席团相见即可。”
结果陈伯达未敢在前台露面,只在118室见了主席团诸公。总理打圆场说:“如此一来,便是中央文革的默认了!”
陈伯达与江青决裂
江青勾结林彪煽起的“全面夺权”,引发“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的无政府主义狂潮,使全国陷于空前的混乱。局势的发展,到了几乎失去控制的地步。
毛泽东迫不得已采取了一系列应急举措,于1967年8月底,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分别实施了隔离审查,并将其羁押于监狱之中(据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所载,1968年1月,对戚本禹亦进行了隔离审查——编者注)。
江青瞬间失去了三位得力助手,悲痛欲绝;然而,她不得不表态“划清界限”,谎称这三位是“刘邓的人”,并声称是自己将他们逮捕的。
陈伯达说:
王、关、戚相继失势之后,江青公然宣称自己有功,非但未有所收敛,反而愈发嚣张。
一位同志曾向我提及:她声称自己守护了“中央三位常委”。显然,这显得颇为荒谬。
自此,除了江青是‘文革’第一首长外,她的女儿当‘文革’秘书(按:为“办事组”组长),事实上一度是第二首长。
江青曾明确表示,对于王、关、戚案件的处理,唯有她本人及其女儿有权涉足,他人无权插手。然而,不久之后,不知何故,她与女儿之间的关系亦陷入了紧张。
当江青造成上述局面,在她女儿还未离开的时候,曾公开在毛主席主持的一次会上,说陈伯达已不住钓鱼台,已不要她们母女,她们愿意回中南海给毛主席当秘书。”

此刻,小组的成员已由最初的十四人锐减至五人: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及一名组员。在七位办事组长(包括办公室负责人)中,有六人(穆欣、王力、宋琼、王广宗、矫玉山、阎长贵)被监禁,唯有江青的女儿李讷得以安然无恙。江青更是将陈伯达在中南海的住所一举摧毁,将他驱逐至新建胡同“安顿”。
陈伯达忍无可忍,跟江青彻底决裂。在其所写《文革小组二三事》中,更加详尽地发泄他同江青、康生等人的矛盾和勾心斗角和他的愤懑心情:
周总理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之后,我仅参与周总理亲自召集的会议,而不再负责召集小组会议。当周总理未在钓鱼台召开会议时,我一般也不再踏入那座位于钓鱼台的“办公楼”(即十六号楼)。
在那模糊的记忆中,我曾在某年不经意间踏入那座办公楼,随意瞥了一眼负责接听电话的同事,随后在会议结束后随意地坐了一会儿。忽然,江青和康生相继到来,而姚文元则住在楼上,一呼即应。江青随即宣布召开会议,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康生也接着发言。他们的言辞,我已难以详述,主要围绕为何未召集小组会议等问题展开。
我只能默默承受他们的责骂,不予以回应。显而易见,我仅凭拒绝召集小组单独会议这一微薄的本事,勉强能够应对江青。
或许是在1968年的某时,我接到一通来自江青的电话,邀请我前往她的住所参加一个会议。我如约前往,只见江青、康生、姚文元三位已经先行到达。会上,江青指出,需要逼迫《人民日报》的一名文艺编辑(编者注:即李希凡)辞职。
我陈述,关于报馆编辑部对历史的审查,我并未发起、参与,也未提出任何建议,怎会是我意图让他死亡?
康生言道:“未曾细读其文,那分明是一封‘绝命书’。”
我说:“我没看到那绝命书。”
随后,江青猛地抓起桌上那只硕大的瓷杯,用力摔向地面,杯子应声而碎,这举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她对我所怀有的极度愤怒。
我察觉到屋外有警卫战士巡逻,若他们发现这堆碎片,定会感到疑惑。因此,我决定将这些碎片逐一捡起,带回到自己的住处,并让那里的工作人员将它们妥善安置于人迹罕至的河沟之中。
若那位文艺编辑不幸遭遇不幸,我将深感罪责深重。然而,康、江二人对任何人的人生际遇皆不萦怀。他们之所以将此事提出质询,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典型表现。
传闻中,江青当时意图任命那位文艺编辑为秘书,为此特意寻找了这样的理由。同样,据传闻所述,毛主席对此举持反对意见,因而该任命最终未能成行。
江青借口将我逐出中南海。
事件发生后翌日,我便搬至新租的居所,意图远离钓鱼台的纷扰,避免再遭受她的欺凌。然而,偶尔我仍会前往那曾经的住所一探究竟。
关于我辞去钓鱼台职务一事,在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一次会议中,江青便趁机对我提出正式的指控,她说道:
陈伯达已不再需要我们,他已搬迁出钓鱼台,另择他处居住。我方与李讷一同返回中南海,将担任主席的秘书一职。
她正暗中施展离间之计。面对这一局面,我选择沉默不语。
在一次会议上,江青言辞坚定地表示:“我与陈伯达之间的分歧,实则源于原则的深刻对立……”张春桥亦在会上对我怒目而视,情绪激昂。
我怒气冲冲,不愿再忍受江青的专横,遂起身离开座位,径直步出会堂。
江青大声道:“我瞧不起你!”
我回了一句:“我也看不起你!”

在中共“九大”会上,陈伯达、康生当上中央政治局常委,江、张、姚当上政治局委员,文革小组就消失了。
此后,陈伯达投奔了“林副统帅”,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遭遇挫败,被捕入狱,随后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他的批判与整顿运动。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与王洪文则结成了“四人帮”,却在1976年10月被彻底粉碎。即便康生去世,也被党中央以反革命集团主犯的罪名,永远开除出党籍。
江青与陈伯达纠纷
作者:王文耀、王保春
在1961年至1970年期间,两位作者曾担任陈伯达的秘书职务。
江青与陈伯达的相识始于延安时期。彼时,陈伯达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而江青主要参与政治工作的机会较少,她的职责主要集中在照顾毛泽东的日常生活。因此,两人之间并未产生任何矛盾。陈伯达回忆称,江青曾两次向他透露出想要离开毛泽东的念头,一次是在延安,另一次则发生在解放初期的北京西山。

▲ 陈伯达(1904-1989),出生于福建惠安。
争文革小组长权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成立了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副组长。江青为了权力,起初处处关心维护陈伯达。当陈伯达因劳累过度生病住院时,江青曾向“文革”小组成员郑重宣布:“小组的大小事情,都要随时请示组长。”
由于江青对陈伯达大献殷勤,陈伯达便写报告给毛泽东,说在他生病住院期间,由江青代理组长职务。这期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群众,江青就代表中央“文革”出席并讲话,大出风头。从此,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就随风转向江青,渐渐远离陈伯达。待陈伯达出院后,江青紧握权力再也不放手。从此,陈、江意见不一,起了矛盾。

江青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不断膨胀,到处发号施令。陈伯达为了约束江青的权力,便找王力、关锋、戚本禹开会起草了给中央的一个报告。报告提出,中央“文革”小组是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下的办事机构,一切言行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擅自做主。会还未完,江青来了,她大发脾气:“我还是不是代理组长,我还是不是第一副组长?”她看了报告的草稿后,立即加上自己的话,并且反复强调说:“我加上的这句是最最重要的!”
毛斥江话未传达
1967年二三月间,陈伯达对我们说,毛主席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对江青的霸道行径严厉地批评过。毛主席生气地说:“有人说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话不对!她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上!她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多次批评过她,她听了吗?她这个人呢,有武则天之心,而无武则天之才!”毛泽东说完后,谁也没有说话。后来,还是周总理打破沉闷的气氛,说:“江青同志确实付出了很多努力,工作辛苦,也是有成就的。”这才使得紧张的气氛得以缓解。
然而散会后,没有一个人传达。可是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还哭闹着诉委屈:“正因为我是他(指主席)的老婆,他总是限制着我。这么多年来,如果不是这样,我早就放开工作了,我真是受不了……”
陈伯达不满地说:“别人做错了事,主席有时生气地批评别人几句,就马上向下传达,被批评的人,很快就会倒台了。而主席这么严厉地批评江青,就没人传达一句,反而还护着她。”陈伯达说完直叹气。
陈伯达与江青厕所纠纷
在1968年的一段时期,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地点转移至了京西宾馆。陈伯达同志由于平日饮水量颇丰,加之年事已高,又有尿频之症,频繁往返于洗手间。宾馆会议室邻近的洗手间门上标有“盥洗室”字样,室内仅设一个厕所,男女并无区分。
某日,陈伯达结束如厕,恰逢江青欲入。江青见陈伯达从内走出,遂怒斥:“你怎敢用我的洗手间?”陈伯达惊讶地查看门上标识,回应道:“这并未标注是您的专用。”说罢,他带着不满的情绪离开。江青怒火中烧,对着陈伯达大声警告:“今日你擅自使用我的洗手间,他日你恐怕要擅闯我的卧房了!”
此厕此后无人敢入。
江青怒摔陈伯达茶杯
在那年的八九月夜幕低垂之际,陈伯达结束了一场于十一楼举行的会议——那里既是江青的居所,亦是她所用的代号。会议结束后,他径直步入了卧室。王文耀得知陈伯达归来,便手持精心挑选的文件卷宗,置于其床前。陈伯达习惯于归来后即卧床阅读,王文耀的这一举动正是顺应了他的习惯。
陈伯达斜靠在床头,目视前方,脸色不是很好,看样子受了很大委屈而又无法对别人说。看到陈伯达痛苦的样子,王文耀吓了一跳。王文耀知道陈伯达的日子一直不怎么好过,便轻声问“你怎么了?”陈伯达低声回应:“没事,只是有些不适。”稍作停顿,见屋内无人,陈伯达便压低声音向王文耀透露:“你不必对外人说起,方才‘十一楼’(江青)对我大发雷霆,甚至摔碎了杯子。”说罢,他从被窝中取出一小包东西递给了王文耀。
王文耀闻言心中一震,接过手中的纸包时,陈伯达低声提醒:“这东西拿出来时无人知晓,唯有‘十一楼’知情。或许她还会要求返还,你打算如何处置?”王文耀回应:“交给我处理。”随后,他又问陈伯达:“她为何对你发怒?当时都有哪些人在场?”
陈伯达轻摇了摇头,长叹一声道:“有康生、姚文元这些人。他们口口声声说是进行研究,然而起初,她便将一封信扔到我面前,要求我阅读,指责我使得写信之人陷入了绝境。康生在一旁附和道:‘那哪里是信,分明是一封绝命书啊!’”
王文耀问陈伯达这个写信的人是谁,陈伯达不肯说,只说:“他是人民日报社的一个编辑,是搞文艺工作的(后来才知道是李希凡)。‘十一楼’说我把他逼上绝路。你们知道,《人民日报》我就没有怎么管,怎么就说是我逼他呢?你不知道,她对我发了很大很大的脾气呀!”陈伯达说着形象地学着江青当时生气摔茶杯的情况:“嘭”的一声,水花四溅,杯碎一地。我担心服务员听到声响进来,便将碎片拾起,用纸包裹。事后,我发现江青似乎也有些懊悔。
携回这些物品后,陈伯达心有余悸,深恐江青会对他产生误会,因而犹豫不决,不知将它们安置于何处。最终,他将这些物品交由王文耀处置,并叮嘱道:“直接丢弃吧,以免伤人。”
知晓内情者皆知,江青的禁忌不可触犯。王文耀手握这包碎瓷片,却踌躇不决。若丢弃,江青一旦急需却无以出示,必将招致不测;而若留存,江青又会质问:“你为何还不丢弃?”经过反复思量,王文耀最终还是决定将碎瓷片暂时保留。当天夜晚,他便将之埋藏于十五楼门前小河畔的松树根下。
过了不久,据说李希凡授意人民日报社一位青年,拼凑了一张江青和毛泽东的合影照片。有一次开会时,江青忽然就着这张照片说:“人家说我要当武则天、慈禧太后,我又没有她们的本事。李希凡有什么历史问题也不跟我说。”陈伯达插了一句:“你说我要逼死他,谁还敢给你说。”江青大声说:“你造谣……我瞧不起你!”陈伯达也顶了一句:“我也瞧不起你!”这时,周总理对江青说:“你是说过的呀。”江青又和周总理对顶起来。
陈伯达愤然离场,沿走廊漫步一周后,再次欲踏入会场。恰逢周总理出门,见状便问:“你为何又回来?”陈伯达领会了周总理的言外之意,遂转身离去,返回了自己的住所。
江青欲摘陈领章帽徽。
1968年下半叶,人民日报社提交了一则涉及日本问题的文件,毛泽东在审阅后作出了篇幅较长的批示。
那是一个夜晚,在人民大会堂三楼的小礼堂内,我们正欣赏着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正当节目尚未落幕之际,陈伯达先生便召见了王文耀,并指示他告知当时在办公室值班的缪俊胜同志,要求人民日报社迅速将文件分发给其他领导同志审阅。小缪同志随即照办。
演出落幕之际,陈伯达提及将前往一楼大堂参与一场宣传口的会议。他事先并未料到,众多中央碰头会的成员亦将出席,该会议由江青担纲主持。会议伊始,江青即要求:“请陈伯达进行检讨,其所负责的《红旗》杂志已有半年未曾出版,且其涉嫌隐瞒主席的最新指示。”陈伯达听闻此言,惊讶回应:“我并未封锁主席的最高指示!”江青反驳:“怎可否认?主席近期就日本问题发布的指示,旁人尽人皆知,你难道不知?”康生在一旁缓缓发言:“我并未收到相关内容。”陈伯达辩解:“我确实看到了指示,并立即进行了传达……”
陈伯达话未完,江青便夺过话筒,打断道:“陈伯达不进行自我批评,我就代替他发言。你身穿军服,头戴军帽。”陈伯达回应:“大家都有军装,并非独我一人。”江青随即追问:“我要剥夺你的军衔标志!你了解红五星的起源吗?”
陈伯达目睹江青此番姿态,心知会议旨在对他进行批判,遂摘下头上的军帽,用力掷于桌面上,高声呼喊:“大字报上街!”此言一出,意在表明他愿意通过张贴大字报的方式,接受批判与挑战。
叶群紧接着举手,仿佛在喊口号一般,高声呼道:“拥护江青同志!”然而,会场内寂静无声,紧张的气氛弥漫。江青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随即严肃地宣布给在座人员:“在此,严禁任何人擅自离开会场,今日会议的内容不得外传,此乃纪律,若有违者,必究其人。亦不得做记录,凡有笔记者,必须放下,方可离开。”话音刚落,江青便继续讲述“红五星的来历”。
散会之后,陈伯达归家,心中郁郁寡欢,情绪沉闷。翌日,他莅临红旗杂志社,在一场全体员工参与的大会上,不吝言辞地发表了一系列消极言论。他言道:“……诸位若有对我之不满,尽可直言不讳,我亦深知自己诸多失误,理应接受你们的严厉批评。杂志半年未能如期出版,非诸位之过,责任应由我一人承担,是我疏于管理,愿为此负责。诸位亦不妨以大字报的形式表达看法,甚至可以将其张贴于街头……”众人听罢,皆感困惑,以为他是在开玩笑。
两日之后,我们自中央办公厅借得那次会议的录音带,王保春、王文耀、缪俊胜三位再次细致聆听。对于江青的无端蛮横之举,我们心中充满了不忿。那盘录音带并未立即归还,而是被妥善存放在我们的办公室之中。
1970年8月,当九届二中全会于江西庐山召开之际,陈伯达因“天才论”遭受批判,此一录音带便引发了我们的焦虑。那时,我们犹豫不决,若将带子退还办公厅,唯恐江青得知后,我们自身难保;若将其留置办公室,亦恐成罪证。在反复权衡后,我们最终将录音带藏于办公室不易察觉的隐蔽处。
江青与中央碰头会对抗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中央领导人员发生了变化,中央“文革”小组人员锐减,陈伯达与江青的矛盾不断,而江青不断向毛泽东告陈伯达的“黑状”。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为工作能顺利进行,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召集人、中央其他党政军领导人参加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来研究重大决策。从此,陈伯达积极参加这个碰头会议,而不主动召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

但是,江青并不满意周总理召开的碰头会议,她多次催促陈伯达召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就一些问题作出决定,与周总理的碰头会议相对抗。陈伯达总以各种借口推脱,拒绝召开“文革”小组会议。江青对此非常生气,但陈伯达是组长,他不参加江青就不好单独召开小组会议。江青很狡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住在钓鱼台,她事先和张春桥、姚文元商量好了,借江青每天晚上请“文革”小组成员看电影的机会来开会。
有一天晚上,陈伯达正在卧室床上躺着看书,钓鱼台值班室来电话说,江青请陈伯达去十七楼看电影。陈伯达一听马上对我们说:“你们告诉他们,说我已经睡觉了。”我们照此转告了值班室。过了没有两分钟,江青又让值班室来电话,说:“康老、江青同志都在等伯达同志。”陈伯达听后急了,毫不掩饰地对我们说:“你们告诉他们说,我已经吃了安眠药睡了。哼!什么看电影,她是又要开小组会,强迫我表态,我不去。你们就说我安眠药已经发作,起不来了。”说着他把被子往上一拉,不说话了。
江青批判新启蒙运动
1968年,陈伯达实在不愿意住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里边,想离江青他们远一点儿。可是新建胡同的家已经被他的妻子刘叔晏闹得不像样子了(刘叔晏正和陈伯达闹离婚),街坊四邻都知道那是陈伯达的家。中办管理局给陈伯达另安的新家——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因房子破旧正在修缮。陈伯达又不想住钓鱼台,管理局无奈就临时将他安排在中南海丙区,国务院这边一个大殿北边,一个很旧的四合院。
这里前后几个院子很长,但几个院子无人居住和办公,非常安静。在那人心惶惶的年代,这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陈伯达很满意,再三对我们说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让“十一楼”(江青)他们知道了。我们当时觉得很好笑,对陈伯达说;“‘十一楼’要找你,去问警卫局你住在哪儿,他们敢不告诉她?”
当时江青、姚文元等正在挖空心思找陈伯达的茬。他们写了一篇批判20世纪3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文章,呈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对江青说他不看,让她找陈伯达看去。一天,江青真的来这儿找陈伯达谈这件事。江青一进院子见到陈伯达便说:“哎呀,这个地方可真不错,赶明儿我也来这住。”江青把准备好的批判文章交给陈伯达。
江青走后,陈伯达既生气,又着急。因为1936年至1937年间,中国文化界掀起的新启蒙运动,陈伯达是主要发起人,这不是直接对着他来的吗?
于是陈伯达就翻阅书籍,找出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肯定新启蒙运动方面的一些言论,让王文耀都抄录下来,经他仔细看后,送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看,他们都表示不同意批判新启蒙运动,这才把那篇批判文章堵了回去,没有让它出笼。
但是,陈伯达并没有忘记江青说要来这个地方住的那句话。为了躲避江青,陈伯达急得不知往哪儿钻。他对我们说:“这个地方不能住了,她还会来的。”他将这件事电话告诉了叶群。叶群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暂时到养蜂夹道干部俱乐部的游泳池边上去住,说是林彪在那儿刚住过,较为安静。
就这样,陈伯达在中南海丙区的大四合院里住了没两天,又匆匆忙忙地搬到中南海外边的养蜂夹道去了。
撕碎了与江青的合影照
中共九大以后,陈伯达住在米粮库胡同,可是他在钓鱼台十五楼的办公室还留着,由缪俊胜留守。陈伯达好久没有去了,想去看看。一天,他去钓鱼台,正巧碰上江青在大院里拿着照相器材,许多身边工作人员陪着,兴致正浓地拍摄风景、人物。见陈伯达来了,江青也为陈伯达拍了好几张,同时还让别人为她和陈伯达拍了几张合影照。之后,陈伯达回到自己的十五楼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但总觉得有些不安,便离开了钓鱼台。
对于与江青拍合影照之事,陈伯达老放心不下,犹豫许久,最后将与江青照相的事告诉了叶群。叶群听后,对陈伯达说:“这可不好,这让主席知道了可不好,江青是什么目的?”陈伯达听叶群这么一说,心里更加不安。江青洗照片都是在新华社,陈伯达马上让自己身边的缪俊胜坐车去新华社摄影部。照片正好洗完,江青还未取走,缪俊胜向摄影部的人打过招呼就取走了陈伯达的照片。
缪俊胜将照片交到陈伯达手中,陈伯达当场就将照片撕成碎片。缪俊胜当时吃惊地说:“哎呀!你怎么给撕了!新华社知道是我取走的。江青同志向我要,我可怎么交代呀!”陈伯达说;“没关系,你就说给我了。”从表情上看,陈伯达的心情一下轻松了许多。
后来,听说江青严厉训斥了新华社,而且提出无她的指示,以后任何人不许拿她的东西。
陈伯达家来了“不速之客”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定了文章的篇数,并排印有清样稿,“文化大革命”初期中断。大约1968年底,陈伯达因无事可做,便决定重新再编。于是他找了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几个人,编起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印出清样以后,报送给毛泽东审阅。过了几天,陈伯达给汪东兴打了个电话,讲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目前出版的必要性等情况,并且问汪东兴毛泽东看了没有,汪东兴告诉陈伯达,毛泽东一夜未睡看完了。陈伯达听了非常高兴。
大约是1969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广场有一个大型群众活动。晚上看过焰火之后,在城楼上休息当中,陈伯达和毛泽东谈话讲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书稿问题时说,里边有几篇文章对当前情况是很有指导意义的,应该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只是说,你先选几篇送我看看。
晚会散了之后,人们都下了城楼,剩下陈伯达、姚文元和新华社国内部的记者在城楼的西侧厅审改当天的新闻稿。定稿之后已经很晚了,在下城楼时,陈伯达和姚文元并肩走着。陈伯达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将他和毛泽东在城楼上的谈话告诉了姚文元。
第二天下午,陈伯达正考虑给毛泽东呈送哪几篇文章时,来了位“不速之客”——江青。江青是第一次来陈伯达这个家,她下车后边进陈伯达家的门,嘴里边嚷着:“哎呀!老夫子在哪儿呀?”进来后。她对陈伯达说,她是刚从毛泽东那儿来的,毛泽东同意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我们大家来分头搞吧,文章由你来分配。寒暄了一阵,江青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书稿放下就走了。
江青走后,陈伯达很丧气,他很不愿意江青插手。陈伯达估计在城楼上告诉姚文元之后,当天晚上姚文元便将这一信息告诉了江青,而江青马上就到毛泽东那去抢了这个差事。
不管怎么样,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总是件好事,陈伯达也有事可做了。但不管陈伯达如何努力,在江青的多方干扰破坏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出版工作没有完成,最后还是被康生总揽过去了。
江青对陈伯达落井下石
在庐山会议即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已被批判。会议将要结束前,陈伯达去求见毛泽东。毛泽东接见了他,很平和地对陈伯达说:“你看你把这个会议搞成这个样子,下一步怎么办?”陈伯达说:“我下农村去。”毛泽东说;“你去找和你一块工作过的同志好好谈一谈……”
陈伯达离开毛泽东住地去找江青。江青一见陈伯达便说:“啊!稀客稀客……”江青自己不和陈伯达谈,而是驱车带陈伯达一起去找康生。到康生那里时,张春桥、姚文元已经坐在康生的会客厅里等着,这似乎是早已准备好的。
陈伯达坐下还没说上两句话,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就同时开火,对陈伯达连讽刺带挖苦。陈伯达被羞辱得抬不起头来。一个大文人受到如此待遇,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几乎当场晕倒。他们让陈伯达准备下次在大会上向大家检讨。陈伯达说:“我现在脑子很乱,无法动笔写。”康生说:“你无法动笔,我代你写。”
康生代替陈伯达写的检讨,用词相当刻薄,陈伯达都难以启齿。没有办法,为了过关,只好忍辱在会上照本宣科。

下山回京之后,陈伯达本想回家当农民,过个平民的晚年。他没有想到被关进监狱度过了18年,期满一年后就去世了。
免费股票配资平台官网,专业炒股配资,国内最靠谱的配资公司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